上周六台灣國民黨換屆,由馬英九接吳伯雄當第六任主席。
此前,馬於七月黨主席選舉中成功取得二十八萬多票(百分之九十二強),故周六只是交接儀式。馬本是第四任國民黨主席,但○七年因綠營指他當台北市長期間,曾非法挪用首長特別費;法庭決定起訴當天,馬即辭去黨主席之職,並同時宣布參選中華民國第十二屆總統,以示清白、無懼審訊。○八年三月,馬在總統選戰中獲勝;四月,特別費案三審定讞,馬獲判無罪;五月,就職總統。上周,馬復任國民黨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台灣人說馬「完全執政」。這種「集權」,和中共黨主席的那種不一樣,因為馬的權力不僅受中華民國憲法約束,現實政治中更須面對反對黨制衡。儘管如此,馬取得黨主席權力之後,的確有利於實現他主張的「以黨輔政」,結束國民黨歷史上一貫的「以黨領政」。不過,馬主席同時是馬總統,「輔」和「領」之間,到底有何分別?今天筆者和大家談談這個問題,因為在大中華民主政治進程中,這關鍵的一步有示範作用,而馬英九兵行險着,以毒攻毒,成敗一線之間,影響可以很大。
一般認為,政治民主化,始於結束一黨專政,中間實行民主普選,形成兩黨或多黨制,經歷幾次政黨和平輪替之後,民主體制即告成熟,民主化便大功告成。如果這樣想,則台灣的民主化已接近完成,但其實不然,因為還欠了那關鍵一步,就是把原來長期執政、專政的政黨「瘦身」、「變種」,還原為一個不具實質管治權力的真正公民組織;在台灣,具體而言,這一步就是把國民黨徹底「非列寧化」,轉變為僅僅一部選舉機器及社會上某種價值觀之下不同管治理念的公開競爭平台。這種性質的平台很重要;一個沒有黨內專權、不論資排輩、不以最高領導意見為所有黨員意見的政黨,最能孕育出活力充沛緊扣時代需要的政治新星(如奧巴馬),最有效地推動社會前進。在一些傳統觀念深厚、人民教育程度較低、公民意識未興的地方如中國大陸,這種性質的政治平台不重要,亦無可能建成,但台灣已經逐漸擺脫這樣的社會形態,舊的政黨模式因此需要改革,才能發揮民主政治中的民智力量。
回顧一下國民黨歷史,有助思考馬英九在這方面的重要責任。辛亥革命後的十年裏,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黨在建設統一的民主國家道路上屢遭挫折,一九一五年有袁世凱復辟,一七年又有張勛復辟,孫先生不得不發動所謂的「第二次」、「第三次革命」,卻始終收拾不了亂局,更一度被迫流亡日本。一九二三年,孫尋求蘇俄幫助,蘇共派出政治顧問包羅庭(Mikhail Borodin),協助孫中山按列寧模式改組國民黨,並資助籌建黨領導的黃埔軍校,締造類似蘇聯紅軍的革命武裝力量。國民黨先前是一批革命家和激進知識分子烏合之眾,自此成為組織嚴密、意識形態鮮明的列寧式政黨,控制一支以黨的政治思想為精神力量的軍隊。這支黃埔軍校培養出來的「國軍」,後來不敵二七年成立、由中共領導青出於藍的「中國工農紅軍」,但那是後話;在當時,國民黨列寧化的確有效,其後在「北伐戰爭」中節節勝利,很快夷平各路軍閥,統一南北乃至全中國。不過,俄國人在一個中國搞了兩個列寧式政黨,結果只能是專制和內戰,以致及後「大江大河」中流的全是中國人的血;兩岸分治之後,更有其他弊端。
李登輝取得國民黨領導權之後,台灣漸次進入現代社會,專制政體必須逐步打破,否則無法有效管治。由於孫中山創立的中華民國法統中本來就有不少民主憲政元素,只不過在國民黨列寧化後幾十年鐵腕統治下成為假民主;這些憲政元素,無疑有助台灣社會在李登輝治下生出多黨政治及其後石破天驚的二千年政黨輪替。但是,即便如此,國民黨內部的專政色彩依然未褪,以至在馬英九執政之後,黨內大老仍可借屍還魂,試圖以黨領政、干政;急統派連戰繞過馬英九,續以其先前築起的「國共平台」主導馬政府初期的海峽政策,便是一例。列寧式政黨,以黨領政是常態,民主化之後,民選出來的總統竟必須聽命於黨內當權派而不是直接向選民負責,這是與民主原則相違背的。
馬英九對憲政有執着,自然不能繼續接受「以黨領政」。但是,他不能完全拋棄國民黨,因為在下一屆選舉中,他還需要一部選舉機器;因此,他只能採取現時的辦法,即重新「奪權」、再當黨主席,並試圖在那個位置上進行國民黨的最後「非列寧化」。這當然有風險;最大風險來自他自己。權力腐蝕,馬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會不會到頭來被權力腐蝕,不僅不把國民黨去權化,還原原本本繼承壞傳統,在自己落任之後還要以黨內大老之尊垂簾聽政呢?很難說。他今年年底如何處理國民黨黨產,將是重要指標,因為黨產是國民黨內部權力的一個重要來源。
skip to main |
skip to sideb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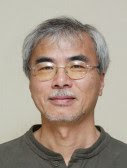
香島論叢 | 香港信報
緣起
香港教育偏重數理商科, 鮮有培育人民、哲學、文科、文化的人材。君不見莘莘學子大塊兒參加奧數競賽, 立志做數學家、物理學家、商界臬雄等, 以丘成桐、陳繁昌、陳省身、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高錕、李嘉誠等為榜樣典範。
孔子曰:「富而後教」。社會多元化, 一個和諧社會, 最終要建立於文化之上。出色的政評、文化人於香港鳳毛麟角。
練乙錚先生文章一針見血, 詞鋒犀利, 希望能給讀者新觀點, 新啟發, 願諸位敬仰練先生學養之餘, 應視之為珍玉, 立志成為未來政評家, 此則乃香港之福。
香港缺乏文化人, 黃霑仙遊後, 吾懷念他的經典作品, 還期待新的接班人再闖高峰呢!
孔子曰:「富而後教」。社會多元化, 一個和諧社會, 最終要建立於文化之上。出色的政評、文化人於香港鳳毛麟角。
練乙錚先生文章一針見血, 詞鋒犀利, 希望能給讀者新觀點, 新啟發, 願諸位敬仰練先生學養之餘, 應視之為珍玉, 立志成為未來政評家, 此則乃香港之福。
香港缺乏文化人, 黃霑仙遊後, 吾懷念他的經典作品, 還期待新的接班人再闖高峰呢!
Blog Archive
-
▼
2009
(39)
-
▼
October
(23)
- 替「大得不能倒」的黨算算數
- 紅黑同體說明黨患上血癌
- 管治威信是如何流失的
- 以微調按揭成數全面取代操控勾地
- 大報為何煽情渲染慳電膽事件
- (貧富懸殊)差距不宜過闊.風險或可少些
- 陸客買樓豈只豪宅 中價環節急升難免
- 改造國民黨 垂範大中華
- 台灣民主化還欠的關鍵一步
- 談社聯窮人數字 論現代社會扶貧
- 美國以負入息稅扶貧優於香港
- 財富拍住美國 窮人一樣咁多
- 產業政策出政績 拆牆鬆綁用公帑
- 經濟不再是香港最大問題
- 公民自治亦可高效分配資源
- 偏見不利早放 遲來還是春天
- 筆戰第二回:金融學「有效市場假說」
- 這場筆戰有看頭!
- 議內勞揭政治盲點 僱家傭損長幼尊卑
- 輸入內傭與輸入活豬的考慮怎能一樣?
- 紅利日薄科技難搞 體制樽頸必須打破
- 中國人口紅利大, 未富先老是隱憂
- 青春三十載 衰老一百年
-
▼
October
(23)
Search This Blog
關於練乙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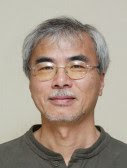
- 練乙錚粉絲
- 練乙錚說,寫香港的政治經濟評論,他給自己定下的準則,是不靠內幕消息。儘管沒有達官貴人「餵料」,練乙錚憑著仔細的考證、嚴謹的分析,他的文章絕對「有料」。他的《香島論叢》,是政經圈中人不能錯過的專欄。
Tags
香島論叢
(35)
香港
(13)
中國
(8)
共產黨
(4)
二零一二
(3)
亞洲
(3)
人口紅利
(3)
扶貧
(3)
政策
(3)
特首
(3)
選舉
(3)
EMH
(2)
Youtube
(2)
人大
(2)
台灣
(2)
土地政策
(2)
家傭
(2)
打黑
(2)
政改
(2)
政改諮詢
(2)
民主
(2)
法工委
(2)
立法會
(2)
經濟學
(2)
草案
(2)
視頻
(2)
諾獎
(2)
貧富懸殊
(2)
選舉法
(2)
金融學
(2)
Paul Krugman
(1)
RTHK
(1)
Writing
(1)
中國火箭之父
(1)
事件
(1)
余錦賢
(1)
信報
(1)
動筆動思考2009
(1)
勾地
(1)
原則
(1)
參選人
(1)
問題
(1)
國民黨
(1)
基本法
(1)
如何流失
(1)
威信
(1)
孔子
(1)
寫作技考
(1)
慳電膽
(1)
房屋
(1)
操控
(1)
政論
(1)
政黨
(1)
效率
(1)
教會
(1)
施政報告
(1)
有效市場假說
(1)
李小薇
(1)
柏林慶典
(1)
柏林牆舊
(1)
校園驗毒
(1)
民主化
(1)
水災
(1)
法制
(1)
無賴
(1)
產業
(1)
筆戰
(1)
算賬
(1)
管治
(1)
築牢
(1)
組織
(1)
經濟
(1)
翻叮
(1)
腐敗
(1)
行為
(1)
訪問
(1)
論語
(1)
諮詢文件
(1)
議事論事
(1)
負入息稅
(1)
貧窮
(1)
逝世
(1)
酬金
(1)
醜聞
(1)
錢學森
(1)
雙普選
(1)
香港脈搏
(1)
香港電台
(1)
騙局
(1)
高錕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