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回歸之後,政府放棄以往在經濟工作中的「積極不干預」哲學,
喊出一些模稜兩可、運用起來自由度很高的口號,逐步向產業政策靠攏。起先,有「最少干預、最大支持」,後來又有「大市場、小政府」,最新的說法則是「拆牆鬆綁」。把干預說成支持,把行政主導的大有為政府說成小,把或明或暗的利益傾斜甚或輸送說成拆牆鬆綁,都很容易,久而久之,物腐蟲生官商勾結在所難免。現時的特區政府官員包括曾特首未必有不軌之心,但取消官商之間的傳統良性隔閡,其不智直如火中取栗。但是,高官予巨賈厚利,巨賈以優差回報,在一些產業政策大行其道的國家非常普遍,日本便是最佳例子,鳩山由紀夫上台,聲言要杜絕此惡習,談何容易。這些經驗教訓,在我國上上下下出現「GDP崇拜」、官員熱衷於急功近利的情況下,漸漸成為「老套」;去年金融風暴發生之後,不少人更因西方國家在財金方面監管不善,如鐘擺般傾向支持政府大力干預市場,忽然間,連凱恩斯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等本與金融監管扯不上什麼關係的政府行為,都東山再起。
自由經濟論者絕非認為市場萬能,政府支持經濟的行為,亦不一定視為不對,例如提供交通基建等具「正界外效應」的設施,更是其職責所在,只不過不應為天下先。先出手捕捉潛在需求而滿足之,是興業家(entrepreneur)的社會角色,要冒很大風險,成功則可享專利(直至市場出現跟風對手),失敗則賠上老本。興業家從試錯得到經驗,敢為天下先且優為之;政府官員性忌風險(不然不會追求鐵飯碗),如果不是受巨賈花言巧語誘惑,一般不會帶頭冒風險搞產業政策。
港英時代,政府提供軟硬基建,一般採滯後政策,即在需求清楚出現、市場顯示明確訊息之後,政府才有所行動,這既是西方經濟自由主義精粹,亦是中國傳統黃老之道的核心內容。這點,西漢《淮南子.原道訓》說得比老聃還清楚:「聖人無為無不為。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謂無不為者,因物之所為。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為先唱,感而應之;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註)。無為政府不是閉上眼睛睡大覺,只不過「不為先唱,感而應之」;靜而後動,反為可「以少正多」。
當然,這不等於說,「先唱」者一定失敗;政府帶頭搞經濟,只要花得起錢,沒有什麼事不能搞出一點名堂來,但錢花得是否高效,卻是另一回事。以港府儲備之豐,就算要無中生有搞一個航太業大概也不成問題,花幾百億,沒有買不到的硬件、請不來的專家;故施政報告要落實經機會提議的「六項優勢產業」,政府付出足夠資源為之「拆牆鬆綁」,終了未嘗不可有所成,但過程中哪位官員要遭遇什麼道德險境,資源成本效益如何計算,就閒人免問。
港府經濟哲學從積極不干預變為事事「先唱」,除了由於回歸之後商界成功發揮力量之外,還因為受內地那套「政府萬能論」(statism)影響。改革開放之後,中央政府不再像從前那樣在經濟環節包辦一切,但政府或黨主導一切經濟工作的觀念依然未變。走資本主義道路之初,大陸無足夠興業者可快速帶動改革實踐,故地方領導幹部負起「為天下先」的角色,也不為過,但九七年的香港情況並非如此,故港府官員要「為天下先」,就很奇怪。筆者認為,除了剛才說的是受巨賈花言巧語所惑,還有另一原因,那就是行政長官或有意角逐此大位者,深明北京領導人都以實幹經濟的魄力和成績作為評估地方主要官員表現的標準,故港人參加行政長官權力遊戲者,必按北京遊戲規則辦事,以保證在經濟工作上的一言一行所作所為,起碼是北京實時看得見、聽得懂的那套。誰要是愚不可及不願「為天下先」,首先便輸了賣相這頭一注;其次,即便是得了大位,若堅持「不為先唱」而經濟上有所成,則因為角色上是成人之美,功勞難證明是自己的,因此又輸尾注。如此,回歸之後,「理性」的特首選擇哪一套經濟哲學,便很清楚。一馬當先打經濟牌推出各種眩目動聽的政績工程,然後動用公帑和行政力量鳴鑼開道拆牆鬆綁以保成功,無疑已成為特首的必殺技(dominant strategy)。這是對十多年來特區政府經濟哲學轉變的一個唯物論解釋。
以推教育產業為例,政府慷慨劃出靚地,低息貸出巨款給財團投資者建一些世界級校舍(不排除投資者夥同某些本地或海外辦學團體),再與內地幹部打通關係,大量學生便可源源抵港,成為創滙大軍,特首於是大功告成,比埋首搞好本地學生教育容易多了。資源成本效益難算清沒關係,反正做幾年便連任,再幾年便榮休,讓下一位推另外的政績工程可也。轟轟烈烈,說穿了就那麼回事。
註:引文略有刪節。
(按:昨文「人口老化問題」段那句「因為人口減少而不成問題的居住問題」,說「人口減少」是早了一些,應該說「人口增幅接近零」。本港人口調查數據顯示,香港人口增加率九六年為百分之一點八,○六年已跌至百分之零點四。)
skip to main |
skip to sideb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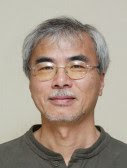
香島論叢 | 香港信報
緣起
香港教育偏重數理商科, 鮮有培育人民、哲學、文科、文化的人材。君不見莘莘學子大塊兒參加奧數競賽, 立志做數學家、物理學家、商界臬雄等, 以丘成桐、陳繁昌、陳省身、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高錕、李嘉誠等為榜樣典範。
孔子曰:「富而後教」。社會多元化, 一個和諧社會, 最終要建立於文化之上。出色的政評、文化人於香港鳳毛麟角。
練乙錚先生文章一針見血, 詞鋒犀利, 希望能給讀者新觀點, 新啟發, 願諸位敬仰練先生學養之餘, 應視之為珍玉, 立志成為未來政評家, 此則乃香港之福。
香港缺乏文化人, 黃霑仙遊後, 吾懷念他的經典作品, 還期待新的接班人再闖高峰呢!
孔子曰:「富而後教」。社會多元化, 一個和諧社會, 最終要建立於文化之上。出色的政評、文化人於香港鳳毛麟角。
練乙錚先生文章一針見血, 詞鋒犀利, 希望能給讀者新觀點, 新啟發, 願諸位敬仰練先生學養之餘, 應視之為珍玉, 立志成為未來政評家, 此則乃香港之福。
香港缺乏文化人, 黃霑仙遊後, 吾懷念他的經典作品, 還期待新的接班人再闖高峰呢!
Blog Archive
-
▼
2009
(39)
-
▼
October
(23)
- 替「大得不能倒」的黨算算數
- 紅黑同體說明黨患上血癌
- 管治威信是如何流失的
- 以微調按揭成數全面取代操控勾地
- 大報為何煽情渲染慳電膽事件
- (貧富懸殊)差距不宜過闊.風險或可少些
- 陸客買樓豈只豪宅 中價環節急升難免
- 改造國民黨 垂範大中華
- 台灣民主化還欠的關鍵一步
- 談社聯窮人數字 論現代社會扶貧
- 美國以負入息稅扶貧優於香港
- 財富拍住美國 窮人一樣咁多
- 產業政策出政績 拆牆鬆綁用公帑
- 經濟不再是香港最大問題
- 公民自治亦可高效分配資源
- 偏見不利早放 遲來還是春天
- 筆戰第二回:金融學「有效市場假說」
- 這場筆戰有看頭!
- 議內勞揭政治盲點 僱家傭損長幼尊卑
- 輸入內傭與輸入活豬的考慮怎能一樣?
- 紅利日薄科技難搞 體制樽頸必須打破
- 中國人口紅利大, 未富先老是隱憂
- 青春三十載 衰老一百年
-
▼
October
(23)
Search This Blog
關於練乙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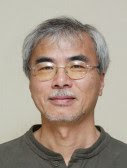
- 練乙錚粉絲
- 練乙錚說,寫香港的政治經濟評論,他給自己定下的準則,是不靠內幕消息。儘管沒有達官貴人「餵料」,練乙錚憑著仔細的考證、嚴謹的分析,他的文章絕對「有料」。他的《香島論叢》,是政經圈中人不能錯過的專欄。
Tags
香島論叢
(35)
香港
(13)
中國
(8)
共產黨
(4)
二零一二
(3)
亞洲
(3)
人口紅利
(3)
扶貧
(3)
政策
(3)
特首
(3)
選舉
(3)
EMH
(2)
Youtube
(2)
人大
(2)
台灣
(2)
土地政策
(2)
家傭
(2)
打黑
(2)
政改
(2)
政改諮詢
(2)
民主
(2)
法工委
(2)
立法會
(2)
經濟學
(2)
草案
(2)
視頻
(2)
諾獎
(2)
貧富懸殊
(2)
選舉法
(2)
金融學
(2)
Paul Krugman
(1)
RTHK
(1)
Writing
(1)
中國火箭之父
(1)
事件
(1)
余錦賢
(1)
信報
(1)
動筆動思考2009
(1)
勾地
(1)
原則
(1)
參選人
(1)
問題
(1)
國民黨
(1)
基本法
(1)
如何流失
(1)
威信
(1)
孔子
(1)
寫作技考
(1)
慳電膽
(1)
房屋
(1)
操控
(1)
政論
(1)
政黨
(1)
效率
(1)
教會
(1)
施政報告
(1)
有效市場假說
(1)
李小薇
(1)
柏林慶典
(1)
柏林牆舊
(1)
校園驗毒
(1)
民主化
(1)
水災
(1)
法制
(1)
無賴
(1)
產業
(1)
筆戰
(1)
算賬
(1)
管治
(1)
築牢
(1)
組織
(1)
經濟
(1)
翻叮
(1)
腐敗
(1)
行為
(1)
訪問
(1)
論語
(1)
諮詢文件
(1)
議事論事
(1)
負入息稅
(1)
貧窮
(1)
逝世
(1)
酬金
(1)
醜聞
(1)
錢學森
(1)
雙普選
(1)
香港脈搏
(1)
香港電台
(1)
騙局
(1)
高錕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