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實體經濟有止跌跡象,看GDP增長率,
中國已經高位回升,法德兩國剛剛從負轉正,美國則第二季度跌幅快速收窄。金融方面,格老於月初着大家留意LIBOR-OIS息差➀,當時,此利息差別已從去年十月十日金融風暴高峰值的二百六十四點止回落至二十八點子,距離正常狀態分界線的二十五點子僅一步之遙;昨天,這個息差值終於「達標」,重返去年風暴爆發之前一月二十四日的二十五點子水平。➁當然,這個水平只是正常狀態的上限,距風暴發生前的十一點子五年平均值尚遠;如果看信貸總量,則目前仍然偏低,尤其是銀行給中、小企業的放款量,更比正常低得多。總的來說,美國可望如去年底一般預測那樣,於今年第三季回復正增長(格老估計增長百分之二點五),法、德二國復元則比預測早一季。如果復蘇走勢持續,則目前這個號稱戰後最嚴重經濟衰退,無論看產值跌幅、失業率,還是看時間長度,都「不過如是」,遠沒有上世紀三十年代那次慘烈。這顯示財金專家預測危機的能力雖無提升,但危機出現之後的控制能力則有所改善;究其原因,大概因為危機成因日新月異難以捉摸,但解決辦法兩百年來不外幾道板斧(增加財赤、削減利率、增加信貸流量等),工多藝熟。
此外,復元過程也往往有跡可尋,比預測危機何時發生容易。災情一旦喘定,企業便負起推動復蘇的主要責任;此時原料價格已大幅下降,僱用人手也十分精簡,管理層在止蝕壓力下,千方百計增加營運效率,故勞動生產力提升一般很快,例如今年第二季美國非農業環節勞動生產力升幅年率達百分之五點五,是○三年以來最高。總成本下降而勞動生產力提高,故企業收入縱因需求減少而下跌,盈利率卻通常在衰退的中後期開始轉正急升;美國第二季度七成以上公司業績勝於預期,不少還有可觀利潤,就是這個原因。企業利潤掉頭回升之後,管理層信心復元,開始增加生產、增聘人手,失業率回落,實體經濟便告復元。當然,為克服這次特大經濟危機,各國投入巨額資金救經濟,故實體經濟回升之際,還有一個從市場回收通貨的善後工作,要由央行做好,以保價格穩定,但這不是大難題(央行向市場注入通貨,有所謂「流動性陷阱」(liquidity trap),但反向則無)。
儘管這次危機造成的破壞,沒有像去年景況最差之時的種種「末日圖像」那麼嚇人,但所帶來的痛苦卻絕對巨大,對貧窮國尤甚。富國金融損失不少,但實體經濟倒退有限,人民底子厚,社會福利制度比較完善,問題說大不大,但窮國就不是那麼簡單;像很多非洲國家,因為金融環節落後,未與國際金融體系連成整體,故基本上逃過危機第一波,但當發達國的金融問題損害實體經濟和政府財政,對第三世界的產品需求和經濟援助都大幅減少,這第二波對窮國造成的損害便很大,甚至還可致命。故研究這次危機發生的原因及政府在發生過程中的處理手法,從中汲取經驗,至為重要。為此,不少經濟學家已坐言起行,有些更已做出結果;先前捕捉不到危機先兆痛失荊州,之後亡羊補牢便先鞭早着。這些研究,大多是建設性的,包括探討如何改善金融規管、怎樣避免某些企業變成「大得不能倒」企業,等等,但有一些研究者卻挑實證題目,做出的結果很出人意外,下面舉一例子。
大家知道,金融大企業處理風險不善,是這次危機發生的重要原因,而不少人更認為,企業高層主管的薪酬合約存在不適當誘因,鼓勵了這些主管過分甚或無限增加企業承擔的風險,結果「車毀人亡」,令股東受損、經濟重創,故這些主管的薪酬合約必須整頓;事實上,所有接受美國政府注資拯救的大企業,其主管薪酬合約已受政府定出條件限制。不過,瑞士洛桑聯邦理工學院和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兩位學者,研究了全球九十八所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在○六至○八年間的風險承擔狀況,及其主管薪酬合約中的誘因條款,發現二者之間並無統計相關,此結論與「傳統智慧」大相徑庭➂;更有一些事例顯示,合約誘因與股東利益比較一致的銀行,在風暴中的業績反而較差!
這個研究是金融風暴之後在有關問題上的第一個,還不能說完全可靠,但如果以後的同類研究指向同一結論,則業界和政府進行改革之時更須小心。看似合理的想法,實證結果並不一定支持,因為事物往往有深層複雜性,非「常理」輕易察覺。這樣的例子,其實並不罕有。
註:➀LIBOR-OIS息差即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和隔夜指數掉期利率之間的差別;此差別增加,反映銀行認為借貸風險增加,預示信貸市場將會收縮;➁另一個常用息差是TED spread,即三個月LIBOR與三個月美國國債息口的差別;此差別去年最高達四百六十五點子,遠期平均是三十點子,昨日按彭博計算是二十七點子;➂見R. Fahlenbrach & R. Stulz, "Bank CEO Incentives & the Credit Crisis," NBER WP#15212, July 2009.
skip to main |
skip to sideb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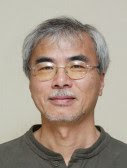
香島論叢 | 香港信報
緣起
香港教育偏重數理商科, 鮮有培育人民、哲學、文科、文化的人材。君不見莘莘學子大塊兒參加奧數競賽, 立志做數學家、物理學家、商界臬雄等, 以丘成桐、陳繁昌、陳省身、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高錕、李嘉誠等為榜樣典範。
孔子曰:「富而後教」。社會多元化, 一個和諧社會, 最終要建立於文化之上。出色的政評、文化人於香港鳳毛麟角。
練乙錚先生文章一針見血, 詞鋒犀利, 希望能給讀者新觀點, 新啟發, 願諸位敬仰練先生學養之餘, 應視之為珍玉, 立志成為未來政評家, 此則乃香港之福。
香港缺乏文化人, 黃霑仙遊後, 吾懷念他的經典作品, 還期待新的接班人再闖高峰呢!
孔子曰:「富而後教」。社會多元化, 一個和諧社會, 最終要建立於文化之上。出色的政評、文化人於香港鳳毛麟角。
練乙錚先生文章一針見血, 詞鋒犀利, 希望能給讀者新觀點, 新啟發, 願諸位敬仰練先生學養之餘, 應視之為珍玉, 立志成為未來政評家, 此則乃香港之福。
香港缺乏文化人, 黃霑仙遊後, 吾懷念他的經典作品, 還期待新的接班人再闖高峰呢!
Search This Blog
關於練乙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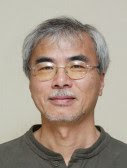
- 練乙錚粉絲
- 練乙錚說,寫香港的政治經濟評論,他給自己定下的準則,是不靠內幕消息。儘管沒有達官貴人「餵料」,練乙錚憑著仔細的考證、嚴謹的分析,他的文章絕對「有料」。他的《香島論叢》,是政經圈中人不能錯過的專欄。
Tags
香島論叢
(35)
香港
(13)
中國
(8)
共產黨
(4)
二零一二
(3)
亞洲
(3)
人口紅利
(3)
扶貧
(3)
政策
(3)
特首
(3)
選舉
(3)
EMH
(2)
Youtube
(2)
人大
(2)
台灣
(2)
土地政策
(2)
家傭
(2)
打黑
(2)
政改
(2)
政改諮詢
(2)
民主
(2)
法工委
(2)
立法會
(2)
經濟學
(2)
草案
(2)
視頻
(2)
諾獎
(2)
貧富懸殊
(2)
選舉法
(2)
金融學
(2)
Paul Krugman
(1)
RTHK
(1)
Writing
(1)
中國火箭之父
(1)
事件
(1)
余錦賢
(1)
信報
(1)
動筆動思考2009
(1)
勾地
(1)
原則
(1)
參選人
(1)
問題
(1)
國民黨
(1)
基本法
(1)
如何流失
(1)
威信
(1)
孔子
(1)
寫作技考
(1)
慳電膽
(1)
房屋
(1)
操控
(1)
政論
(1)
政黨
(1)
效率
(1)
教會
(1)
施政報告
(1)
有效市場假說
(1)
李小薇
(1)
柏林慶典
(1)
柏林牆舊
(1)
校園驗毒
(1)
民主化
(1)
水災
(1)
法制
(1)
無賴
(1)
產業
(1)
筆戰
(1)
算賬
(1)
管治
(1)
築牢
(1)
組織
(1)
經濟
(1)
翻叮
(1)
腐敗
(1)
行為
(1)
訪問
(1)
論語
(1)
諮詢文件
(1)
議事論事
(1)
負入息稅
(1)
貧窮
(1)
逝世
(1)
酬金
(1)
醜聞
(1)
錢學森
(1)
雙普選
(1)
香港脈搏
(1)
香港電台
(1)
騙局
(1)
高錕
(1)


